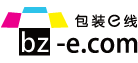当春节鞭炮声为逝去的旧年画上休止符的时候,寻常的百姓习惯给自家算一笔账、做一个总结:这一年里,我付出了什么;这一年里,我又得到了什么。一个个普通家庭账本上的涂涂写写,连聚起来,就变成了宏观经济脉动的节奏器。
新京报记者深入全国各地,采访了农民、工人、小老板、网红、创业者等多个群体,听他们讲述自己过去一年中平常或不平常的故事,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打拼一年的“账单”。
靠“量大”维持,不敢跟客户说“不”;
收入不如意造成一批从业者离职,有的转行做公务员、教师、券商
“刚干了一个月外贸,打算去券商了。”陈思纯(化名)告诉新京报记者。与一年前出国留学时相比,神情有点落寞。她以为进到了一个一月能挣好几万的行业,但四五千块的“死工资”让她选择了转行。
工作三年的赵明则从外贸助理变成了公务员,“我们国贸班一共38人,现在还在做外贸的,也就3、4个。”工资不如意是他们离职的原因。
从数据上看,2016年的外贸并不算差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,中国出口13.84万亿元,下降2%,连续第二年降低,但与风雨飘摇的2009年相比,已经增长了一半以上。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表示,去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前低后高、稳中向好的走势。2017年我国外贸的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,所面临的困难也不是短期的,但无论外部市场如何波动,“我们都有信心应对。”
从业二十几年的宁波外贸企业主老周表示,现在行业面对两个对手,一个是东南亚国家,还有一些是中部地区的工厂。原材料涨价对他造成了冲击。年前他第一次寻求去国外参展,内贸也成了他的转型考虑。
新京报记者 宓迪 浙江报道
遭遇“内外夹击”,招工一年比一年难
老周在宁波拥有一家纺织外贸工厂。
2008年,老周曾遭遇过危机。“当时看着旁边的打火机厂一个一个倒闭,心里就开始着急了,”他说,“拿不到订单,全厂的几百号人等着吃饭。”他压缩了库存规模,辞掉了很多工人,终于慢慢渡过难关。
一家工厂春节期间招聘外贸业务员
“今年总体情况不错,年终奖也发了。”老周说,“我们这一行有两个对手,一个是东南亚一些国家,还有一些是现在中部地区的工厂。”
“像越南这些国家,给出去的钱比我们低,但是我们在大风大浪里也好几年了,完全根据客户定制的产品,在质量上还是有信心的。”老周说。
更大的挑战,则是来自国内的因素。“现在中部地区给员工的待遇也起来了,招工是一年比一年难。”老周说,“同样一份工作,这边四五千块钱的普通工人,只要老家那边肯给三千,他们就不出来打工了。”
实际上,老周给他的操作工八小时3000到3500元一月,年年都有增长,增幅200-300元左右。
“多挣不了几个钱,谁愿意背井离乡呢?”老周反问。
不过中部地区也有劣势。“虽然工资便宜,但配套辅料的生产工厂还沒有完全转移,离港口远,运输成本高。”老周说,“在宁波一个40尺高柜拖箱费3500元,而河南到青岛(港口)的费用要7000元,几乎是一倍。”
去年以来,人民币对美元价格震荡走低。但在老周眼中,货币贬值对出口带来的利好受到了原材料涨价的冲击。
他给记者展示了数月前与助理来往的微信纪录,微信中助理告诉他,“现在拷边线(纺织业的一种原材料,下同)涨了2200元一吨,皮圈比以前涨了145元一袋,打包带比以前高了15元……除了人工,其他都涨了。”
在外贸行业中,约定汇率、报价都是根据先前的价格而定,通过信用证付款,收到钱往往在好几月后。若是这两项数值变化过大,就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。
老周说,今年总体经营还可以,但主要也是靠“量大”在维持。
经过2008年的危机,让他看清楚一件事,做生意要主动求新求变,不然坏时候可能随时找上门来。年前他去了趟迪拜参展,这是他第一次去国外参展。“像德国、美国,今年也有计划。
内贸也成了老周的转型方向。“现在也开始接一些内贸的单子,做得还不错。”